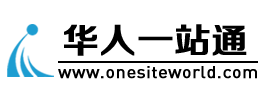呵,走在张爱玲住过的楼里呢,简直不是真的呀……脚下的淡黄色方块地砖,明快的色调。兴奋在喉咙里几乎喊出来,虽然她不在楼上了,然而,这个人就是有气场的,头顶有一双眼睛,令我简直扭捏起来,脸热著,不好意思极了。走过三楼的转角,蓦然间,我眼前一暗,满头晕眩,紧接著,一阵无可比拟的锐痛,仿若脊椎被刺透,同时我的胃里有翻江倒海一样剧烈的痛楚。我呼吸吃力,太阳穴胀痛,双脚失重,连一只脚抬高迈上一级台阶,瞬间也变得不可能了。脚下踩著的那淡黄的方块瓷砖,感觉那么遥远。我心想著坐下去歇一口气,这个动作也不可能完成了。友人说话间,不见了我的声音,回头见一张瞬间成鬼的纸白的脸,登时吓住了。叩开了楼梯前的一扇门,对著门内的人缓缓陈情:我们是来看张爱玲的—打扰了,如此这般……可不可以,叫我们借用一下洗手间?
“这就是张爱玲以前的家呀。”里面的人见多识广,截断了我们声情并茂的诉说,淡漠地一摆头:“进来吧。”
就这样,我登堂入室地,走进了张爱玲居住过的寓所,一径推开浴室的门。救命的皇天!我拧开水龙头,激烈地呕吐起来,自脊椎处起的,感觉躯干被拦腰斩断的锐痛,开始减退。恰如痛楚的被确定, 此时,亦渐渐自脊背处抽离,缓缓的,徐徐抽离的轻松—-我的呼吸顺利了,洗一洗脸,理一理头发,又活过来了。清凉的水流哗哗声里,我听见了从水管深处,那种赫赫的声音。张爱玲形容过的,“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,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,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,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。即便你不去太岁头上冻土,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。”

是一间宽大的浴室,有宽大的外开的窗户,地砖上搁著一只浴缸,盥洗盆的镜子旁边有一只小柜,墙壁凹进去一间橱柜大小的凹橱—–隔了五十年,还是看得到摩登。空间宽阔且实用。然后我想到,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敲门进入。是来自于她,来自于空冥之间,时间场深展处,另一方的回应——我用这样的方式,进入了她五十年前的旧家。这一念,令我顿时喉头发紧,眼底生泪。
细条子镶木地板,宽大的客厅,有一个穿堂去往另一间房子,玻璃窗外看得见上海的天空,灰蓝的,一径辽远开去,这房子再是物是人非,依然有一种西式的沉潜摩登。来看她的男子,在笔下形容过她的寓所,“有华丽的兵气”。她在这里渡过了一生之中最流丽的时光,与姑姑相依为命,写字,逛街,看橱窗,吃甜食,著奇装异服,与男子恋爱,为之心碎。似乎上海人都认识她,即便她只是去弄堂里的小印刷厂看书稿,身后也跟了弄堂的小童们,拍著手齐声叫张爱玲张爱玲—在她身后,那样的小童历朝历代从来不曾消散,今日来看她寓所的我,即是其中一个。
她喜欢上海,“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:脏与乱与忧伤之中,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,使人高兴一上午,一天,一生一世。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,宽敞,笔直,齐齐整整,一路种著参天大树,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…….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——还没离开家就已经想家了。” ——-等我读到她这番话时,她已经去国离乡半世纪了,再也不曾回过上海。只是,这样的对故土的表白,让我心痛。
我站在2006年初夏,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盘桓过的阳台上,一朵艳黄的丝瓜花外是江南初夏的天气,铺出去的上海灰蓝的天,楼下是四敞八方的马路,公寓对面是电车的终点站,一个萍聚萍散之地。从这个角度看出去的上海静安,时间依然是张爱玲的。这地方,天然就是有著一种山长水阔的散发之意,这,就是张爱玲的地域—-所有的离去都不会再回头,所有的告别都不会再重逢。
2009年的春天,天南地北每个张迷读完《小团圆》,都是一副恍然大悟长吁短叹的样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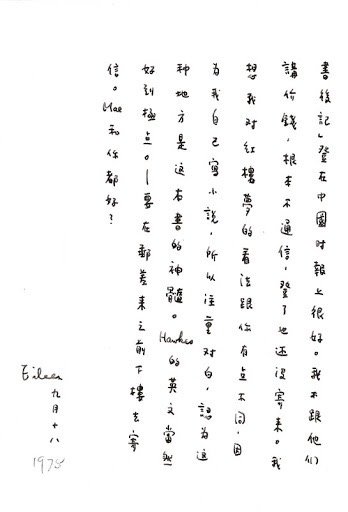
还有,胡兰成,我们多少是有些错怪他了。从前,读《今生今世》,看他细致地写张爱玲从上海寄钱到温州雁荡山,一笔不漏,到张爱玲与他决裂时,还寄了一笔钱,因为彼时他是在天涯亡命途中,虽是决裂,也还是为他的生计著想的。我们后来的这些读者,在这粗鄙下贱,男女互害的时代里,穷惯了,穷怕了,恶形恶状地算计惯了,每回读书,都忍不住要扳起手指算一算,胡兰成到底花了她多少钱,如何地德行无耻又恬不知耻地花女人的钱。然而,读《小团圆》,我们看到了,胡兰成(邵之雍)为了迎娶张爱玲(九莉),登报声明离婚。又抬了两箱子钱来交给她,为的是张爱玲一直说,要还钱给母亲的,所以他交了一笔钱给她,为她预备著,将来把钱埋在深红的玫瑰花下,还给母亲,扬眉吐气地以示决裂。我们这些—–在这个粗鄙下流的时代,从没有被善待过的女性读者,顿时就觉得,胡兰成待她,满好的,他是顾惜她的。若是张爱玲不与他决裂,他大抵也如任何一个在漫长的婚姻里,居家日子里头的男人那样,有点小小的四顾徬徨,左顾右盼,沾荤惹腥一番,又悻悻地缩回脖子,缩回身子,回到婚姻中来。如张爱玲在小说《倾城之恋》里说所描写的二战时的香港,一对男女 在战时结为夫妻的情形,“流苏拥被坐著,听著那悲凉的风。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,灰砖砌的那一面墙,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。风停了下来,像三条灰色的龙,蟠在墙头,月光中闪著银鳞。她仿佛做梦似的,又来到墙根下,迎面来了柳原,她终于遇见了柳原。……在这动荡的世界里,钱财、地产、天长地久的一切,全不可靠了。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,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。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,隔著他的棉被,拥抱著他。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。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。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,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。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,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,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,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。”
“两人一同走进城去,走了一个峰回路转的地方,马路突然下泻,眼前只是一片空灵──淡墨色的,潮湿的天。小铁门口挑出一块洋磁招牌,写的是:”赵祥庆牙医”。风吹得招牌上的铁钩子吱吱响,招牌背后只是那空灵的天。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,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,突然打起寒战来,向流苏道:”现在你可该相信了:‘死生契阔’,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?轰炸的时候,一个不巧──”流苏嗔道:”到了这个时候,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!”柳原笑道:”我并不是打退堂鼓。我的意思是──”他看了看她的脸色,笑道:”不说了,不说了,”他们继续走路,柳原又道:”鬼使神差地,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!”流苏道:”你早就说过你爱我。”柳原笑道:”那不算。我们那时候太忙著谈恋爱了,哪里还有工夫恋爱?”

张爱玲是洞彻人性的,她似乎从不信任在流逝的时光与人山人海所组成的洪流中,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有著凝固的不朽的钟情。人和人的际遇,莫不是因缘聚散罢了。然而轮到她自己,她还是茫然又热烈,世界上一切经验在她那里都不算数——她是一棵树,一直费力地,费力地往邵之雍(胡兰成)的窗前生长,在阳光里,风吹著叶片哗啦啦的,是她大声在呼喊:我在这里,我在这里!
虽然,到末了,她和他之间,到底没有超越平常男女之间的窠臼——男人的屡屡犯规和回归,女子的忍耐担待到最后的忍无可忍。